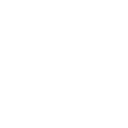不管設計一個科學的醫保付費制度有多難,都不該將壓力傳導給醫生,不該讓本就辛苦工作的醫生內心流淚。
據報道,浙江省某市腫瘤醫院醫生陳明紅今年2月份又只拿到了1000元的績效獎金。最近半年來,因他所在的呼吸內科醫保經費超標,全科的人都被扣錢,獎金只能按保底金額發放。
醫生因超過醫保基金限額影響收入,此類現象在很多地方可以說屢見不鮮。醫保控費從上到下,存在一個壓力傳導途徑,醫保部門將控費目標與醫院獲得的基金份額掛鉤,影響到醫院的收入,醫院為了實現目標,將控費與科室和個人的績效獎金相關聯,將控費壓力分解給科室和醫生。
醫生也有辦法將控費壓力轉嫁出去,比如當醫保患者住院達到一定的期限后,不管疾病是否治愈,都勸他們出院。或者一到年底,就拒收醫保患者。這些現象在部分省市每年都會多次發生,近日出現了“住院15天必須出院” 的新聞,在醫療界引發熱議。
據報道,家住廣州天河的范先生最近幾個月輾轉了5家醫院,如今再次面臨“被出院”;家住廣州荔灣的黃女士已經被“15天出院”困擾了整整5年,其父親患有中風后遺癥、血管性癡呆、心梗等疾病,從2013年住院至今,5年內反反復復經歷“被出院”的尷尬遭遇。因為大部分醫院都規定,只能住院14天或15天,從該家醫院出院后,至少要轉兩家其他醫院,第三輪才能重新轉回來。有的醫院甚至規定,一年內不能在同一家醫院住6次以上。
反反復復的轉院,帶來的不僅是家屬不停奔波,還有各種檢查費用的疊加。而這一切的源頭,都指向爭議已久的“醫保限額控費”。
為什么要控費?
醫保之所以要控費,說白了就是沒錢了。近年來,公立醫院的醫療費用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的態勢,這不僅“稀釋”了國家對于醫療改革的巨額投入,而且也對醫保造成了巨大壓力,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醫保見底”的情況。
隨著醫保基金不堪重負,于是很多地方推行了醫保總額付費制度,讓醫院承擔超支風險,以確保基金收支平衡。通常來說,醫保部門根據各醫院上年度的門診量和出院人數,按照一定的增長比例,確定醫院本年度的醫保費用總額。如果費用超額,醫院自己消化。
醫保部門給醫院定指標,實行醫保控費,醫院當然也不傻。為方便管理,醫院直接從而將“醫保定額”像切蛋糕一樣分到科室,科室當然不能科主任背了,也下達到醫生個人。最終,這個“鍋”還得是醫生來背。
雖然對醫保部門來說,他們的本意是希望通過新的報銷制度限制醫療費用,同時也為防止醫保騙保,避免醫保浪費,但在藥品零加成政策后,不少醫院收入下降,誰也不愿意多承擔損失。因此,醫院也只能把這部分錢轉嫁到醫生的頭上——現在醫生不但要看病,還要每天花心思計算醫保費用。
以至于不少醫務人員都曾經這樣吐槽過:“現在到醫院看病用藥不是醫生說了算,而是醫保說了算。”
于是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醫生為了避免“多干多賠”,只好“看菜下飯”,多收自費病人,少收醫保病人。為了醫保不超標,干脆要求患者15天就出院,甚至很多醫生表示,自己的家屬住院也是如此,不然“真的賠不起”。
按病種付費有效嗎?
為了防止上述情況出現,醫保局又想出了新招:按病種付費。以廣州為例,自2018年1月1日起,由市醫保局與定點醫院按病種分值付費方式,結算醫保參保人的住院醫療費用,“按病種付費”被寄予厚望,希望減少“15天被出院”等分解住院的違規行為,一旦定點醫療機構有分解住院、掛名住院等行為的,當次住院的分值不計算,還按該分值的3倍扣分,由此約束醫院自覺遵守規則。
然而問題又來了。從已經實施按病種付費的地方來看,褒貶不一,引發了不少新問題:“一口價”后,醫院費用包干,醫生是否會在診療過程中盡量節省,甚至偷工減料,以求最大限度地控制費用?既要控制總費用,還要控制自付比例,醫療安全怎么保證?
對于根據第一診斷付費的“單病種付費”規則,醫生同樣有應變辦法。醫生可以無視并發癥,不理會第二、第三診斷的疾病,還可以讓患者分次住院,或者轉到其他科室,將第二、第三診斷當成第一診斷再次住院。醫生甚至可以把診斷下得更重,通過一個不太靠譜的診斷抬高限額,等等。
所以,假如醫生不想因不可控的原因突破限額,最終,風險和壓力就會轉嫁給患者。患者處于壓力傳導的最底端,往往只能默默承受。
總的來說,醫保支付制度的出發點是好的,其目的是遏制過快增長的醫療費用,避免醫保“蛋糕”被吃光。但是,任何政策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夠的。如果醫保部門 “只問結果、不問過程”,只看醫保基金是否超支,無疑是一種“懶政”思維。醫保與醫院互相博弈,本是為了維護患者利益。但按照現行情況來看,患者反而成了“犧牲品”,背后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值得思考。
醫保制度的制定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涉及到醫療各個環節,我們不能一味批判,但也希望制度能夠更加貼近醫務工作本身,而不是只出發于一個美好的愿景。新醫保局的設立,行業人士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將給醫保帶來哪些新的改變,能否讓醫保制度更合情合理,我們拭目以待。
最關鍵的是,在計發醫生待遇時,應禁止將醫保控費情況與收入掛鉤。規定醫生薪酬不得與藥品、化驗等收入掛鉤,是為了避免過度診療。但是這一做法卻從另外一個極端導致醫生消極治療。如果控費情況不與醫生的收入掛鉤,則可讓醫生進行正常治療。至于過度診療或其中產生的一些醫保浪費的情況,完全可以采用第三方方式加以監督。否則,處于壓力低端的患者必受其害。
總之,無論如何,處在醫保付費末端的醫務工作者和患者都不該成為壓力的最終承擔者。醫保付費怎樣設計才更科學,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但相信結合醫務實踐,我們終能摸索出一條更合理更公平的途徑。到醫生個人。最終,這個“鍋”還得是醫生來背。